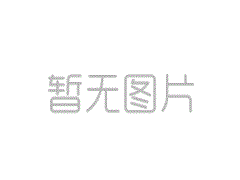去年年末,综艺《戏剧新生活》获得了“2021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真人秀”。
节目里,黄磊、赖声川、乔杉和另外八位默默无名的戏剧人,一起在乌镇住了两个多月,把戏剧工作从业者的生存现状、创作过程、演出状态一一真实展现在大众面前。
赵晓苏是八位戏剧人之一。综艺录制前,他是首届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单元最佳剧作的男一号,与孟京辉、赖声川等资深戏剧导演合作过,参演过一系列先锋实验性话剧。但在大众视野里,他始终是一个“无名戏剧人”。
综艺播出后,一些戏剧人的形象变得丰盈和具象,赵晓苏也变得“更有名”了。去年秋天,他第六次启程奔赴乌镇戏剧节。某种意义上,他已然成了一张乌镇的“戏剧名片”。许多粉丝为他而来,在飘着小雨的江南小城排队等待了六小时,只为了看一场他参演的戏剧作品。
但对赵晓苏来说,他从事戏剧从“不为钱想,因为挣不到太多钱,也不为名想”。他爱戏剧的干净与纯粹,他会把“我可以死,戏剧不能亡”挂在嘴边,他在个体生命中也运用着“戏剧思维”。只要走进深爱的剧场,把自己交给舞台,在幻想边界,就没有什么能把他拖回世俗。
以下,是赵晓苏和戏剧的故事。
旺盛表演欲在涌动
1986年春天,赵晓苏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传统家庭,父亲是军人,母亲是医生。
这个北京男孩从小就嘴贫,爱接茬儿。
初一时,他拉上另一位也“特贫”的男生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圣诞演出。那天,台下乌泱乌泱的,坐着全年段16个班的学生。赵晓苏穿了件最漂亮的毛衣,和搭档俩人抬头挺胸、“倍儿自信”地上了台。他们即兴发挥来了段相声。
“没演过,连排练都没排,上台后逮着什么说什么。”他们面前支着两根立麦,但俩人说兴奋后,站偏了台,离话筒越来越远。观众听不清他们说什么,开始小声嘀咕,可是赵晓苏“丝毫不觉得尴尬”。
不过,在父母面前,他一直小心隐藏着这份表演欲,“没让他们见着”。
有一次,他偶然看到迈克尔·杰克逊跳舞的录像带,被彻底震住了,“这真就是巨星啊”。他趁着父母上班的空当,锁上房门、对着电脑,偷偷模仿起当时流行的“太空步”。
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后,赵晓苏的表演欲得到了更彻底的释放:“我还和一个一米九的黑人在舞池里跳舞battle过呢!”
那天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:他穿着一身杰克琼斯和一双小皮鞋,身旁的黑人比他高出一个头。一束聚光打在舞池中央,两个人在黄白光晕里卡着节拍、舒展肢体、控制肌肉。DJ看俩人跳嗨了,重新给了个更激烈的beat,气氛被瞬间点燃。周围黑暗中,沸腾的人群挥着手,为他们尖叫欢呼。
“要不人家怎么老说我是‘蹦迪专业’毕业的,”赵晓苏回想起青春年少,不好意思地笑了,“无知者无畏嘛,现在让我battle,我可不敢了。”
大学期间,赵晓苏不太爱上课、常常不交作业,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“好学生”。但等上了台、有了观众,他的表演欲就全展现出来了。
某次台词课期末考核,老师让每个人说段绕口令。轮到赵晓苏上场,他立刻起了范儿,故意给自己设计了不少“戏”。“飞个眼神,来点互动,不只是口齿清晰地念段绕口令,我演的还挺高兴。”最后,赵晓苏拿到了很高的分数。
小时候,赵晓苏就喜欢观察模仿别人的言行举止:讲评卷子的老师、调皮捣蛋的同学、边哭边吵的情侣……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都是他的模仿对象。在中戏课堂,这个特殊爱好得到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。
“赵晓苏是全年级学猴子学得最像的。”年级组长看完他的动物模仿,当着所有人的面这样说。
在他父母眼里,舞台上的儿子拥有他们从未见过的另一面——外放、肆意、热烈。
赵晓苏曾目睹父母日复一日、循规蹈矩的人生。他们的生活被条条框框束缚着:“母亲早上六点半出门,父亲是七点半。下午五点半,俩人再下班回家。”他内心慢慢生长出另一种声音:“我长大后绝不这样,够够的。”

戏剧舞台是他为自己找到的出口。从事戏剧表演,没有复杂的人情世故,情绪表达是高昂干脆的,还可以与观众直接互动。
这些都让他感到舒服。
用七年,换一次和偶像的针锋相对
2006年,他加入了孟京辉导演的《魔山》团队。
《魔山》是一部大型儿童舞台剧,投资超千万。正式演出那天,演员们都将登上首都体育馆的舞台,面对台下近12000名观众。
主创团队里有不少国家话剧院的演员。赵晓苏离开校园环境,第一次接触专业话剧团队,立刻遭到当头一棒:“那里和学校不一样,大家都太强了。”
那时,导演孟京辉会给每个人布置作业、让大家交段子。还是学生的赵晓苏感受到了差距:不管是基本功、表演节奏,还是气场、肢体表达能力,自己都不太行。“交作业好像老比不过人家。”强烈对照下,赵晓苏深深体会到挫败与失落感。
国家话剧院演员、导演陈明昊当时也是团队一员。赵晓苏至今记得他强大的舞台感染力:“他站在那儿,就是发着光,我那时才知道什么是个人魅力。”
话剧是直面人的表演,演员们甚至能感受到黑暗中观众的呼吸。首演前夜,赵晓苏一宿没睡,他从没在一万两千人面前演过。对他来说,除了要克服紧张,和陈明昊共同登台是另一大挑战。在《魔山》里,赵晓苏和陈明昊都负责演“坏蛋企鹅”,但赵晓苏内心始终犯怵:“你让我站他旁边说段独白,我那会儿肯定不敢。”
巡演结束,赵晓苏心里无比清楚:自己需要提升基本功。
戏剧人说的“基本功”并不是简单的声台形表,他们毕生追求的是“鉴别力与执行力”层面的增长。后来,他常在小剧场跑演出。为了演好一个办公室白领,赵晓苏专门去了广告4A公司实习,去了解“他们都干什么、怎么生活的”。
在小剧场锻炼了两年,赵晓苏正式签约加入孟京辉团队。
在孟京辉导演的音乐剧《空中花园谋杀案》里,赵晓苏饰演首版赵大夫。原作者史航认为,“赵大夫”涉及多个层次的表达诠释,是个“非常难演的角色”。

赵晓苏离开排练厅、回到家,经常自己坐着,也不说话。他观察着母亲作为医生在日常里的行为举止,想从中提取可以用到表演里的素材。在他脑袋里,还装着关不掉的“感受开关”和一个“人物库存”。不论是一个人走在路上,还是和朋友喝酒海聊,他永远在观察与感受,陌生人某个不经意的神态都可能带来灵感。他会默默记下,加入库存,想着下次表演可以用上。
每一次排练,其实都是他的尝试与创作:这一遍加点“京油子”态度,下一次用“滚刀肉”(指死皮赖脸、纠缠不清的人)的感觉,再下次试着改变节奏、多点停顿。他在看似重复的调整中,不停寻找最适合的表演方式。
正式登台那天,他的演绎让编剧史航印象深刻:“以后看别人演的时候,我脑子里老在跟晓苏的演法在对照、在印证。”

2013年,导演杨婷联系赵晓苏,邀请他和陈明昊一起合作悬疑喜剧《开膛手杰克》。
那时,赵晓苏已经积累了几百场演出经验,但等到第一次排练,面对偶像陈明昊,他还是心虚了。毕竟,在赵晓苏看来,陈明昊可是“白素贞”,自己不过是一个“只修炼了几年的小蛇妖”。
最初说台词时,赵晓苏有些扭捏,试图用花招为自己打造一个罩子,来掩饰表演上的慌张与不自信。
“赵晓苏,你没把最真实的一面交给我!”陈明昊吼了一嗓子。
那之后,赵晓苏开始卸下保护罩、排空杂念。他慢慢明白,“那些招在艺术家面前都没有用,舞台上应该踏踏实实的”。白天排练结束了,他还常和陈明昊黏在一起,继续交流各自对剧本和人物的理解。喝酒、谈戏,他们一起度过了许许多多个夜晚。
三月的一个晚上,北京先锋剧场响起了《Casey’s Last Ride》,赵晓苏和另外两位演员陈明昊、赵红薇走上台鞠躬、谢幕。

《开膛手杰克》正式落下帷幕,赵晓苏在戏中一人分饰六角。有位剧迷对他的表现感到意外:“按照以往经验,最替与陈明昊同台的演员们捏把汗。但这次的男演员(指赵晓苏)表演节奏流畅到你想为他叫好。与陈明昊这样的演员对戏,他竟然没有乱了分寸,还以他的柔适时地克了陈明昊的刚。”
七年前,赵晓苏还是个不敢在陈明昊身旁念独白的青涩学生。但这次,他终于和偶像稍微“针锋相对”了一下。
我可以死,戏剧不能亡
“戏剧到底挣不挣钱?”
《戏剧新生活》第一集就抛出了这个现实问题。大概十年前,赵晓苏也面临过艰难的抉择。
在孟京辉工作室待了三年多,赵晓苏主动选择离开。
当时,每个月到手的钱不多,他还陷入前所未有的表演瓶颈期。在先锋、实验性戏剧之外,他对更具体的人产生了好奇,想在“坚实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去做表达”。这是他尝试影视剧作品的初衷。
但是,想完成这种转变并不容易。赵晓苏笑称自己身上带着“北京孩子的劣根”,不争不抢的。作为影视领域新人,赵晓苏没有资源,也不习惯带着目的性与人打交道,结果显然易见——他得不到工作机会。
在赵晓苏的人生弹簧里,离开孟京辉工作室后的一年都是被“狠狠压扁”的日子。他“一个人沉甸甸地待着”,胖了、蓄了胡子、没有工作和收入。最艰难的时候,他甚至不得不开口向父母要钱。
这些年,他逐渐获得了一些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,但严格来说,赵晓苏也从未完全离开过戏剧舞台,他继续跟着陈明昊尝试了一些疯狂怪诞的戏剧作品。
2015年,陈明昊导了一部先锋实验话剧《公牛》,戏台即拳击台,职场上复杂的人际关系、冲突都被抽象表达为一场血腥暴虐的拳击赛。赵晓苏饰演的托马斯,是一个在职场饱受欺凌的角色。观看《公牛》时,观众也可以加入其中,成为戏中人,参与到对托马斯的“施虐”中。

有一次,演出地点在北京的愚公移山俱乐部,赵晓苏穿好厚实的防爆服上了台。
封闭且昏暗的空间里,煽动性的音乐流动,人群狂躁着、呼喊着、宣泄着。“我演的是托马斯,其实台下欢呼嚷嚷的每个观众都是在生活里受气的托马斯。”
这时,一个情绪爆发的女观众冲上台,抄起一个空饮水机桶道具,朝着“托马斯”的头,用力挥打下去。
通常,在防爆服保护下,痛感并不会太敏锐,但赵晓苏那次被打懵了:“饮水桶从头上下来,我听见自己脖子嘎嘣儿一声,当时真吓坏了,我怕我脖子断了,但我想的不是我就死了,我想的是脖子断了,这演出怎么办?”
“后来我又感受了一下,脖子没断。”于是他忍着疼,恍恍惚惚的,坚持演完了全场。
结束后,他脱下演出服,才看到全身多了几十处青紫。庆功宴上,痛感变得更清晰火辣,脖子疼、胯疼、肩膀疼……但这份痛觉也让赵晓苏确信,他真的成为了戏中“被打击、被戏弄”的托马斯。
“演之前知道会发生这些吗?你完全接受这些?”
“未来一定是未知的,人生也是这样,你模拟不了。提前预设的一定没有现实赤裸裸地来到你面前残酷。”
当然,不少观众认为他们太过“癫狂”,发出“何必如此”的质问。但对待表演效果,这群戏剧人似乎总有些“无法理解”的执拗和追求。
《戏剧新生活》里有部环境戏剧叫《倒影》,演出地点在水剧场,主舞台被新月形湖泊环绕。排练时,另一位戏剧人丁一滕想体现不一样的表演质感,提议以“共同跳入湖水中”作为戏剧结尾。

赵晓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那是乌镇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。即使到了下午两点,温度也在零度左右。镜头里,他们聊天时的哈气清晰可见。
冲撞、扭打、跃起,坠落。冰寒的湖水压得两人瞬间喘不上气。
“咱剧场里哪儿有水啊?(这)在平时剧场里实现不了。这几年演的没一个戏是安全的。所以我接受这个。”赵晓苏谈起这些,总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。
节目里,赵晓苏曾半开玩笑地说:“我可以死,戏剧不能亡。”他愿意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戏剧,无论是痛苦还是美好,他都想体验一把。
戏剧融入生命分秒
第一次见面那天,赵晓苏脖子上挂了个树脂材质的机器人手作,眼睛圆滚滚的、表情呆萌。那是赵晓苏在乌镇戏剧节市集上买的,家里还挂了一排,他喜欢这种可爱有趣的小玩意儿。

舞台之外,他在生活独角戏里也一直奉行着直接、较劲的人生态度。
三年前,在朋友影响下,赵晓苏决定报个英语班学习,“就是想进步”。
他走进某家英语培训机构,还没等前台的销售开口介绍,赵晓苏就果断地付全款报了名。有几回,课程难度增加,赵晓苏没能完全理解吸收。下课后,他就一个人坐在教室里,对着讲义,反复琢磨消化。“不学会不罢休。”赵晓苏特意向工作人员要来了机构大门的钥匙。
凌晨十二点,赵晓苏是最后锁门离开的人。
有一次,他和史航老师直播连线,身后背景是一幅1000张的哆啦A梦拼图。为了拼好它,赵晓苏不停不休、连续奋战了18个小时。“我就是这样一人儿。如果我凌晨想吃铜锅涮羊肉,我可以不睡了,但我必须吃着。”

“那在生活中感到焦虑和痛苦怎么办?”
他化用崔健《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》里的一句歌词作为回答:没有感觉才是最大的病。痛苦与焦虑,同样是可以用来感受与享受的情绪。
“我生活中不拒绝任何东西,睡不着就睡不着,享受它,记住这种感觉。”赵晓苏有这种熄不灭的渴望,“因为有戏剧存在,我觉得痛苦也不是痛苦。”
因为敏感,他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周边人细微的情绪变化。
一场演出前,戏剧人刘添祺因太过紧张想要呕吐。赵晓苏察觉后,立马替他揉着肩膀,轻声安慰道:“不要排斥这种紧张的感觉,包裹它,让它成为朋友,跟它谈话,别让它过分影响你。祝你玩儿得开心。”
日常生活中,赵晓苏说话声音是轻的,习惯变换着语气调侃、模仿别人,表达方式偶尔夸张。和他聊天,你不用担心对话悬空。他思维活跃,聊到兴奋的时候,“戏精状态”还会不经意流露出来——
采访那天,北京天气难得的好。赵晓苏坐在咖啡厅靠窗的位置,把整个人泡在阳光里,仰头、闭着双眼说:“啊,阳光真好,想象自己在海滩!”
在之后的几秒沉默里,一时分不清这究竟是舞台上还是现实中的他。
今年上半年,他即将回归舞台,搭档演员黄圣依出演赖声川导演的作品《让我牵着你的手……》,饰演契诃夫一角,开启全国巡演。

“戏剧在你的未来版图里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?”
“很重。”赵晓苏眼神坚定。
只要走进深爱的剧场,把自己交给舞台,“在幻想边界就没有什么能把我拖回世俗”。